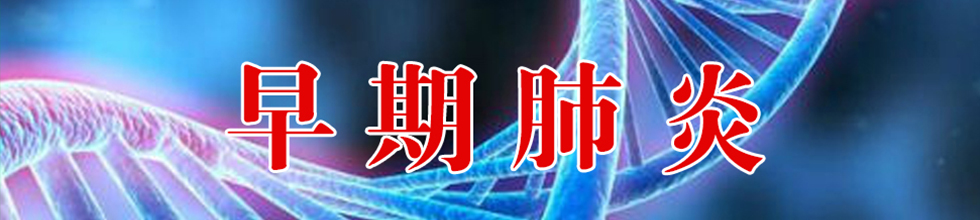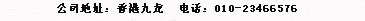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综合防治思路与方
来源:早期肺炎 时间:2021-6-20
北京那个医院治疗白癜风较好 http://pf.39.net/bdfyy/bjzkbdfyy/临床救治的思路与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社会公众往往把中医称之为“慢郎中”,我们的一些中医人,也是自认“擅长常见、慢性疑难杂病防治和养生保健……”,这种话语有时还泛起在政府的有些公文里,更多见的是自年抗击“非典”之后,中医一直被阻挡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的门外边。这样究竟是否属实、公允?如果不析明这一答案,中医就永远是一只脚都踏不进传染病攻坚战的队伍里,当然要谈“振兴、发展”,也就只能是一种痴心妄想了。笔者从年起,就已把视焦瞄向了中医急重病救治的历史考察和现代验证,无论从经典著作还是随后的诸多典籍记载,大量的证据都表明,中医对于急重症救治,如同对普通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一样,都具有丰富多彩的方法及比较理想的疗效,至于因为多种原因所致的手术落后、医疗设备应用不足等,并不能代表主流,更不能以之覆盖全部,尤其是在应对十分特殊的瘟疫流行方面,中医学不仅有如前所述的精彩战略指导,同样也有很多令人叫绝的救治技艺,而且他们从《黄帝内经》到《伤寒杂病论》《瘟疫论》《温病条辨等》乃至近代的诸多续篇,居然都是一脉相承,甚至在应对变幻多端的不同病种瘟疫时,都是一样地有效。回想年“乙脑”暴发,著名中医学家蒲辅周先生以既有的温病辨证理论为指导,用98个处方救治了例患者,无一例死亡;年“非典”流行时,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带领他的团队,依然以既有的温病辨证理论为指导,收治了58例病人,创造了全部治愈、没有病人转院、没有病人死亡、没有医护人员感染的“三个零”奇迹,类此者还有很多。这难道不是中医学强大生命力的表现吗?尤其是在与西医学的一种方法、一种药物只是对一种传染病有效相比时,那不更显得它是一种世界奇迹吗?所以在参与应对上,我们首先必须有足够的勇气与信心!在面对瘟疫病时,无论何人,第一个下意识的问题,就是它由什么病因所致?对于本次全球流行的新型肺炎,现代医学在前期通过病理检验,已经认定是“新型冠状病毒”所致(之所以要冠以“新型”二字,缘在于与年的“冠状病毒”相似而稍异),它具有传染性强、潜伏期长、多靶点攻击(初始在肺,随后可波及肝肾脑等多个脏器)的特点。据报道,截至年2月25日,我国病理专家团队一共完成了11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病理解剖,证实其病变与SARS有类似之处,从前期的病理结果来看,一些死者的肺部切面上,能看到有黏液性的分泌物,刘良教授提示说:“在治疗上如果黏液成分没有化解,单纯用给氧的方式,可能达不到目的,有时候会起反作用。因为正压给氧的时候可能会把黏液推得更深更广,会加重患者的缺氧”。这也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药“清肺排毒汤”等系列方剂有效作用的重要机理。但在冬季已过、春季来临的时节,结合世界其他国家的既有情况报道,是否需要考虑病毒会否变异?其中是否有流感病毒的存在或替代?在中医而言,大家立足于湖北地区紧依长江、冬季大雾、民众好食野生动物的习俗,公认为是“湿毒疫”致病,而从陕西方案临床证治以“寒湿束表”开头,甘肃方案临床证治以“温邪犯肺”开头、推荐处方为麻杏苡甘汤加味或羌活胜湿汤加减,可知西北地区病邪性质也有一定差异,新近先后由方邦江、齐文升等编著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中西医结合防控手册》将之整合为“湿、毒、瘀、闭”,王琦、张伯礼等编著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中医诊疗手册》更将之归结为“湿、热、毒、虚、瘀”,可见,由于地域等因素的影响,一病之下,病因病机却是多样的,这也是中医的一大特点和优点。这些真知灼见,无不来自于开创带着护目镜望诊、隔着防护手套切脉先河,凭着仁爱精诚之心坚守患者身旁的一线同道们,在这里,我们理该为他们点赞、致谢!病因既明,重点就是论治了。从现代医学而言,杀灭病毒就是毫不含糊的中心任务,问题是拿什么杀?能杀得了吗?从现有的事实看,几无理想药物和方法可用,即使既有的拿手药(例如免疫制剂、抗生素、维生素、激素等等),都是在以一例例鲜活生命的煎熬或消失而反证其勉强和无奈,年“非典”时侥幸获救却又生不如死的患者,更在不停地倾诉着超剂量激素的深重罪孽,唯一的救命稻草,只剩下新疫苗横空出世了,关键是这个间期需要多长?前期有效疫苗投入使用后,病毒会不会又发生了变异?……,在过去,一些人总是习惯用西方文化的视角,对中医、中国文化、甚至对中国的政体评头品足说三道四,而当像新冠肺炎这样残酷无情的瘟疫降临时,这个东西却又像一位十分威严的评价师一样,对中西医乃至中西方文化给出了一个公正的评判,足以使人们重新矫正失误已久的是非理念。相反,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古老的中医疗法在此却是依然有效,甚至是游刃有余。中医如何解释呢?就病因而言,他不象现代医学那样——完全陌生、从未谋面,而是“似曾相识”、并不陌生。但在治疗机理的阐述上,有一种流行说法:中医并不在于杀灭病毒,而只在于通过增强人体正气,使得病邪无法伤害人体,人与病毒可以并存。若如此说,经中医治疗过的人,岂不都成了一时间不会发病的病毒携带者?既有病毒携带,倘若人体阴阳气血受某种因素影响而失调时,会否复发?怎么能确保不会传染别人?以我之见,由外传入的病毒与原生于体内的肿瘤细胞不可同日而语,中医对于病毒致病的基本治疗机理,应该是使人体正气得到了有序调动和整合,从而一方面是改变原有环境,使得该病毒逐渐丧失生存、作祟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形成三维性正力,从而将该病毒逐步围而歼之,并排出体外,之后保留于体内的只是抗体,而不是病毒,大家绝不能牵强地用“带瘤生存”的机理去比拟理解。这一观点,还可从吴又可《瘟疫论》所述“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大凡客邪贵乎早逐”、“邪不去则病不愈”、“有邪必逐,除寇务尽”等精辟论述中得到印证。
上一篇文章: 陈鸿驰两谈ldquo莨硷类药物对症治
下一篇文章: 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管理推荐
关于新冠肺炎的救治,主体框架应该在外感病范畴。遥想当年仲景先圣曾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自建安纪年以来,尤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气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为《伤寒杂病论》”。由此可知,其所言“伤寒”即是典型的瘟疫,这也是一部伟大巨著诞生的直接原因之一。该书传至宋代,经林亿等人校编,遂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后人又称前者为“我国第一部外感热病学专著”、“方书之祖”,再奉为“四大经典”之二,随之,它的适用范围便从瘟疫一病扩大到了所有外感病种。这一衍化,也完全符合《素问·热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五十八难》“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的精神;目前的诊疗实践,也已证明了它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因此,无论比辨病辨证论治法则(尤其是八纲、六经辨证纲领),还是论选方用药施治护理,《伤寒论》都是当前必当尊奉的首部宝典。
纵观全国各地的中医救治实况,中药口服是为主流,究其用方,有偏重仲景方者,有偏重温病方者,有兼而取之者,也有重用时方者,然而,无论有何侧重,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中医外感病学的主线,及其间伴随着的内伤杂病学发展成就,这些“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无疑都对此次抗疫发挥着巨大的支撑作用。但是,当前的盛况并不能说明中医学的能力已经得到尽然的展示,其间仍然存在着一些学术上的亟待完善提高之处:
1、“寒温统一论”的现实指导意义不可忽视
中医温病学派从唐宋元明代孕育,至清代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三焦辨证”创立为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一改既往以温燥方药治疗热病的弊病,使外感病的防治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延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北京中医学院赵绍琴教授著作《温热经纬》,提出把卫气营血辨证纲领与三焦辨证纲领合二为一,江西中医学院万友生教授则进一步提出把伤寒六经辨证纲领与卫气营血辨证纲领、三焦辨证纲领统归于八纲辨证纲领之下,进而推出了著名的“寒温统一论”,在这杆旗帜下,古今外感病学派的成就即可得到大融合,对于临床证治具有更大的现实指导意义。面对当前的新冠肺炎救治,这一理论尤其显得适宜、实用、大有用场,实当掀起学习研究应用高潮。2、中药服用切当完全恪守辨证论治宗旨“辨证论治”之辞正式首见于《伤寒论》,究其理义,一方面是指治疗大法,就是“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另一方面强调在护理上,就是“桂枝汤将息法”——“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复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不汗出,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其意是说:患者进服汤药后,就应该配合进服热稀粥之类的清淡温热饮食(切忌厚腻生冷等),如果病状经服一次药即解除,后面的药就可停服不用;如果病症尚在,就可隔2——4小时连服第二、三次,半天之内可把1剂药服完,1天24小时之内尚可进服2——3剂药,其中包括夜间也要按时服药。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尚有其每日服药4次自治中风偏瘫者;金元·李杲《东垣试效方》更有将普济消毒饮1剂共为细末,其中半剂以蜜和丸逐一在口中含化,半剂以温开水冲服的范例。纵观当今新冠肺炎防治,大家公认其基本病因是“湿毒”,存在寒化、热化的病理趋势,故而将清解湿毒列为一切预防与救治方案的基本原则之一,再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取化湿、燥湿、利湿以及清热祛痰等的不同,因为证法合宜,故能少有失治者。但是问题在于能谨守后项者却系鲜见,憾在大多都是口喊辨证论治,实则大兴教条刻板、水不济火,若在生命垂危之际,还是每日1剂药分2次口服,真能见效者,理应谓之侥幸,实当认真反思!3、重视体质分类是提高救治疗效的重要参照“辨证论治”的第二大精髓,即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而“因人”的内涵之一,即在于强调患者体质类型的重要地位,它不仅体现在根据患者的体质类型而实施预防,更着重在临证时的处治上,切勿忽视对其体质状况的了解和融入。例如:平素湿浊偏重者,就可考虑在藿香正气或三仁汤的基础上去加减;平素如果偏肺脾气虚,此时就应考虑用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之类去加减;平素如果是肾有虚、瘀,那么,以地黄汤加减去补肾养精活血化痰便应成为基本治疗思路之一……其余均可依次类推。尚需提醒的一点,还在于医者在对患者的自觉症状进行收集时,一定要严谨下笔,例如患者在自觉全身无力时,若有动则气怯(少),甚或心悸,即可用“乏力”描述,治则就应选用补气的方药;但若“身重如带五千钱”,胸闷体重,不愿挪动,或挪动吃力,就应该以“身体困重”来进行描述,施治选方无疑当以除湿为主了,二者有虚实本质的不同,此时若还是以“乏力”来描述,诚属误导,为医者不可不知。体质与当下的病状之间,前者为本,后者为标,临证只有共性与个性结合、主次有别、标本兼顾,才能避免“虚虚实实”误诊误治之弊,切实发挥既定的救治功效。4、治疗方法、途径多样化是实现既定治则的重要保证清·徐灵胎曾著有《用药如用兵论》,提出对于一些病症的治疗应“多方以治之”,旨在阐明临证治疗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以治疗目的的完整落实为准则,现今用之于新冠肺炎救治,亦然十分恰当。纵观本次的中医抗疫行动,可以说初期由于主在探索摸底,故而从披露的信息来看,其整体诊治都比较拘谨,治法主要是口服汤剂;再看10天后的报道,则是不仅方便对症的中成药一一出列,品种多样、应用简捷、疗效显著、贮存方便的中药免煎颗粒剂和中药注射剂也开始大显身手,更有喜者,医院里,心理、健身功及舞蹈、饮食等也成为重要治疗方法,医院里还出现了用针刺舒调肺气、有效改善患者呼吸功能的信息,全国针灸学会也推出了相应的防治方案,“综合治疗”已然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相比之下,真正投入的中药注射剂品种明显偏少,鼻饲中药、直肠滴注、穴位贴敷等法的应用也是少见,其实,患者在病情危重期间,由于口鼻遮盖着氧气面罩,口服中药不便时,这类给药法实可独辟蹊径,为中医药疗效的更好发挥提供有力支撑;再譬如:肾康注射液本由黄芪、大黄、红花组成,听其药名在为治肾,殊不知其按照中医理论分析,则是功在补气化瘀通腑,用于新冠肺炎救治岂非一员猛将?举此一例,余当类推。5、辩证看待现代医学检测指标从年抗击“非典”,到本次新冠肺炎防治,重要特点是充分应用西医全程防护优势以保工作人员自身安全,全力开发现代仪器检测优势以利确诊,积极发挥中医药治疗优势以提高疗效,中西医的有机结合,大大减少了误诊率和副作用、治疗周期、后遗症,显著增进了有效率和痊愈率、康复水平,委实促进了新时期的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但从近期的报道来看,有极少数经以西医药为主治疗后核酸检测阴性的患者,出院不久又重新出现核酸检测阳性,也就是说面临再次感染或传染的风险。据分析,此系前期治疗时应用了大量抗生素和激素,硬性压低了特征性指标,其内在环境却尚未能得到彻底改善,患者依然处在机能低下或失调状态,精神、饮食、二便等要素都还处于低水平,一旦用药停止,特征性指标也就很容易反弹。其实,这种情况原本是长期存在于西医临床中的,只是在此时出现,直接关系到控制传染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临证者不得不加倍注意。至于应对的办法,一是在早期治疗时就尽量少用或不用抗生素与激素,二是在既用之后及早介入中医药物和其它多种康复疗法,通过人体正气的迅速恢复,防治病毒因素的死灰复燃。临证者理应经常保持这种意识。6、建立整体的防护意识先贤叶天士之所以被后世推崇为中国温病学第一大家,首在于他通过杰作《外感温热篇》树起了温病学的重要构架。例如在病因传播途径方面,他说:“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此之所谓“上”,大多学者都认为是指口鼻上窍,可是这次新冠肺炎的传播,有很多例证都显示,病毒有通过眼睛传播的可能,按部位而论,眼睛也在“上”的范围之中;另外,还有说从大小便中检出病原体者。所以,本次凡是进入隔离病区的医护人员,不但要穿着全身严实的防护服,而且新增了护目镜,实现了全身无一露外者。本人认为,无论是预防还是治疗、是否进入隔离病房,重视眼睛的常规护理和药物保护,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总之,当前的最优化决策,应该是尽可能最大化地客服一切偏见、短见,最快、最大努力地发掘应用眼前的一切有效措施,全力争取最快、最好的疗效。有哲人说:多种病原体对人类的侵扰任何时候都不会休止,我们决不能停留在某一时段,只针对某一种病,而是要考虑长期的应对、防护措施。实为高明之论!回顾近些年来发生的传染病流行问题,在中医看来,其实都是旧问题的重新排列组合,所以我们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的理念与方法,同样也可用于今后其他病原体的防控。固然,不断加强对中医学的复习与深化,不断履行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广泛实践,不断提高根据体质经常性地进行调节,维持阴阳平秘,实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能力,就应该是每个公民、尤其是中医、中西医结合学人的基本任务和神圣职责。(本文原作于年2月,年6月修订未曾正式发表、报奖)作者简介赵斌(.5----),男,汉族,甘肃成县人中医内科主任医师。从1972年8月起,跟师、专业学习中医至今,在认真积累临床经验,擅长中医内外妇儿等全科诊疗的基础上,并先后实现了以“四大学说”(中医学物质理论体系、中风病辨证论治新体系、输液反应辨证论治体系、中医异物病因学说)和“四大疗法”(中医综合疗法、覆吸疗法、小剂量速治法、中医灌肠突击疗法)、2个创新专利(一种持续给药的握药套、一种持续给药的覆吸罩)为代表的系统学术创新。先后发表《浅论中国传统科学的物质体系》、《中风病辨证论治补要》等学术论文92篇;独著出版《杏林探幽》(24万字)、《中医综合疗法》(34.3万字)、《报晓曲》(14·6万字)等书3部,合著出版《中国中医药最新研创大全》(万字)、《中华效方汇海》(52万字)、《医古文注译解析》(24万字)、《常见病的中医特色综合治疗》丛书(分17册,万字)等7部;另有《中风病辨证论治新体系的创建与应用》、《关于中医学物质体系的研究》等8项课题先后荣获省市县“科技进步奖”;并曾应省内外学术组织邀请,先后赴省内外进行学术讲座交流。故此,曾先后13次荣获“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甘肃省名中医(第二批)”、“甘肃省优秀专家(第七批)”、“全省医德医风先进个人”、甘肃省第四批及五级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陇南市领军人才(二批次,第一层次)”、“陇南地区跨世纪学术带头人”等称号;并先后被选举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脑心同治专业委员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脑病学分会常委,甘肃省中医药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副会长,甘肃省中医药文化专业委员会(首届)副秘书长,甘肃省中医内科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副主任委员,《甘肃中医》、《西部中医药》杂志编委会委员,陇南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政协陇南市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委员,政协成县委员会第六、七、八、九、十届常务委员等职。其事迹曾先后被《中国中医药报》、甘肃《发展》杂志、《甘肃科技报》、《陇南报》等多家媒体多次报道。编辑:杜鹏飞审核:赵斌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soyingyong.net/fyzqzz/73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