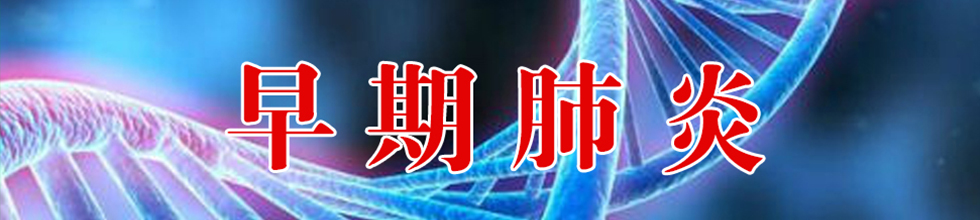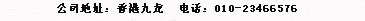卒中相关性肺炎的临床研究进展
本文原载于《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年第11期
本文作者:方芳舒怡肖志杰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脑卒中发生率逐年上升。卒中相关性肺炎(SAP)是脑卒中后常见并可能预防的并发症,与脑卒中不良预后显著相关[1]。SAP是指脑卒中发生7d内非机械通气患者合并出现的肺部感染疾病谱。对于脑卒中发病超过7d的肺炎,医院获得性肺炎(HAP)[2]。SAP发病率为7%~38%[3,4],神经内科重症患者约21%[5],鼻胃管营养患者约44%[6]。SAP是脑卒中患者病死率最高的并发症,占卒中相关死亡人数的31.2%[7]。一项大型队列研究显示,SAP可使脑卒中患者30d死亡风险增加3倍[3]。此外,SAP会延长住院时间,增加治疗费用,提高严重残疾的发生率[3,8,9,10]。早期识别SAP高危患者可能有助于加强个体化监测和实施具有针对性的有效预防措施[11]。1 SAP的发病机制1.1 卒中诱导的免疫抑制(SIDS):
SAP传统上被认为是继发于由吞咽功能受损及其他多方面因素如意识水平下降、卧床、机械通气等引起的误吸和吞咽困难[12]。然而,与仅有吞咽困难或意识障碍的患者相比,脑卒中患者SAP高发病率提示其发病机制可能涉及其他免疫学机制[11,13,14]。SIDS是缺血性脑卒中大脑损伤后特异性的免疫应答,在脑卒中24h内迅速发生并持续数周[15]。人体其他器官损伤后一般引起中枢神经系统(CNS)发出强有力的抗炎信号;而在缺血性脑卒中发生过程中却产生针对受损脑组织的局部和全身免疫抑制,抑制炎症反应。大脑具有免疫豁免的特性,血脑屏障(BBB)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缺血性脑卒中发生后BBB完整性被破坏,渗透性增加,各种免疫细胞(CNS固有的免疫细胞和循环中的免疫细胞)被募集到受损脑组织,受损局部的免疫表型暴露,产生免疫反应对抗CNS自身抗原,加重脑损伤[16]。SIDS可阻止自身免疫,减轻脑损伤[17];但同时又会引起循环中的免疫细胞减少,增加感染并发症的风险[18]。
1.1.1 自身免疫:
脑卒中发生后,机体的后天免疫可识别受全身免疫系统保护的自身表位并产生应答,称为自身免疫。SIDS被认为是一种后天免疫,可抑制自身免疫对抗CNS抗原,有助于阻止脑损伤加重[16]。当脑卒中患者发生感染时,可导致全身炎症,使患者更易对CNS抗原产生自身免疫[19]。有研究表明,脑卒中大鼠注射内毒素后发生感染,可增加辅助性T细胞1(Th1)介导的免疫应答和大鼠死亡率[20]。此外,获得性感染的脑卒中患者可产生对髓磷脂碱性蛋白和胶质纤维酸性蛋白的免疫应答,与无感染的脑卒中患者相比,其预后更差[21]。
1.1.2 交感神经系统(SNS):
SNS在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的联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SNS过度激活肾上腺素能神经元引起SIDS。过度活化的肾上腺素神经元末梢可诱导SNS进一步活化,从而引起肾上腺髓质和周围器官的神经末梢分泌儿茶酚胺[22]。儿茶酚胺通过β-受体作用于免疫细胞减少促炎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增加抗炎因子白细胞介素-10(IL-10)的释放。β-受体拮抗剂可减少脑卒中小鼠细菌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提示儿茶酚胺在SIDS中具有重要作用[18]。
1.1.3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素轴(HPA轴):
SIDS与HPA轴的糖皮质激素分泌过量有关。下丘脑通过感知脑卒中产生的炎症标志物激活HPA轴;然后肾上腺的束状带分泌过量的糖皮质激素,减少淋巴细胞数量并打破促炎/抗炎因子平衡[23]。糖皮质激素具有抗炎作用,而过量的糖皮质激素会抑制人体的防御能力并导致免疫抑制。入院前使用全身性糖皮质激素与脑卒中后短期死亡风险增加有关[24]。
1.1.4 副交感神经系统(PNS):
PNS主要通过由迷走神经的传出纤维构成的胆碱能抗炎通路来调节大脑和全身的炎症反应[25]。胆碱能抗炎通路作用于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α7(nAChRα7)。脑卒中可通过刺激nAChRα7调节大脑中的小胶质细胞,减轻炎症反应,保护神经细胞免受氧化应激和改善功能恢复[26]。此外,脑卒中后机体的肾上腺皮质可调节胆碱能抗炎通路并下调TNF-α表达[27]。
1.1.5 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
脑卒中可导致脑组织内大量神经元、神经胶质细胞和血管损伤,这些结构受损可通过释放DAMPs来触发炎性小体和激活先天免疫[22]。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热休克蛋白(HSP)、三磷酸腺苷(ATP)、SB蛋白、硫酸肝素、DNA、RNA、氧化低密度脂蛋白、β淀粉样蛋白和透明质酸等都是由非凋亡性死亡的细胞(或免疫系统细胞)释放的内源性DAMPs,其目的是触发无菌性免疫反应以及维持组织稳态。脑卒中发生后,脑血流低灌注区细胞出现坏死,释放HMGB1,从而诱导单核细胞亚群扩增和促进机体在脑卒中亚急性期出现免疫抑制状态,使患者易患肺炎[28]。一项实验研究表明,在脑卒中亚急性期,采用药物或基因工程的方法阻断HMGB1和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介导的模式识别受体信号通路,可减轻细胞的免疫抑制并恢复淋巴细胞的活化状态[29]。
1.2 肺-脑相互作用:
在SAP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肺部与大脑如何相互作用目前尚不清楚。但有研究表明,抑制胆碱能抗炎途径以及释放糖皮质激素、儿茶酚胺和DAMPs可能参与其中[16]。P物质(SP)是参与咳嗽和吞咽反射的重要物质。药物阻滞多巴胺D1受体可以抑制吞咽反射,并减少SP释放[30]。老年吸入性肺炎患者血清SP下降,而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可增加血清SP浓度,降低吸入性肺炎发生率[4]。卒中后口腔菌群谱迅速发生改变,革兰阴性菌定植较非脑卒中患者更为常见,可能也是SAP发生机制之一[31]。目前已从脑卒中患者的痰液中分离出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等多种细菌[32]。但分析既往研究成果发现,即便在95%的脑卒中小鼠血和肺组织培养中发现大肠埃希菌[20],在后续大规模脑卒中人群验证研究中仍不能确定其就是致病菌[33]。因此,阐明SAP发病机制和明确其致病菌对于发现特异性治疗手段以减少脑卒中后细菌并发症非常关键。
2 SAP的预测指标2.1 人类单核细胞白细胞DR抗原(mHLA-DR):
SIDS的特征为全身细胞免疫应答下调,表现为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快速减少和单核细胞的功能性失活,导致SAP的易感性增加[18,34,35,36,37,38]。mHLA-DR表达降低提示免疫功能受抑制[37,38]。年发表的SAP独立预测因素研究(PREDICT研究)表明,mHLA-DR作为SIDS的独立预测指标,是SAP风险的独立预测因子[39],mHLA-DR表达量与SAP发病率呈正相关,正常mHLA-DR患者不会发生SAP。
2.2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
NLR是全身炎症和感染的标志物。NLR比传统细菌感染标志物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超敏C-反应蛋白具有更好的预测价值[40,41,42,43];并且NLR的高低与肺炎严重程度关系密切,NLR越高,提示肺炎越严重[44]。NLR指标简单,获取方便,有助于尽早筛选SAP高风险患者并予以及时干预,也是一种观察抗菌药物治疗效果的临床指标。
2.3 心率变异性(HRV):
HRV可反映脑卒中后免疫调节和感染相关的自主神经系统活动,IL-6和C-反应蛋白表达增高时,HRV也增加[45]。HRV指标包括:极低频范围内的功率(VLF)、低频范围内的功率(LF)、高频范围内的功率(HF)、标准化LF、标准化HF。LF反映交感神经活性,HF反映副交感神经活性。一项前瞻性研究表明,采用动态心电图观察显示,发病48h内的脑卒中患者急性期若无感染证据(WBC和C-反应蛋白),但出现下述HRV改变则提示随后的感染风险增加:标准化HF增加,标准化LF减少,白天LF/HF比例降低,夜间LF和VLF下降[46]。
3 SAP的危险因素及SAP风险预测量表3.1 SAP的危险因素:
目前普遍认为SAP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年龄65岁)、男性、糖尿病、高血压、心房颤动(房颤)、充血性心力衰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卒中前独立程度〔改良Rankin评分(mRS)〕、卒中严重程度〔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脑卒中亚型〔牛津郡社区卒中研究(OCSP)分型〕、吞咽困难、误吸、机械通气、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使用抑酸剂、口腔卫生及菌群移位、住院时间长(20d)等[47]。
3.2 SAP风险预测量表:
近年来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促使研究者对SAP的危险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制作出多种SAP风险预测评估表,对脑卒中患者进行SAP危险分层并预测SAP发生,在脑卒中患者个体化管理、制定治疗方案和预后评估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3.2.1 A2DS2评分表(年龄、房颤、吞咽困难、性别、卒中严重程度):
A2DS2评分表由Hoffmann等[11]于年在Stroke杂志发表(表1)。数据来源为至年柏林卒中登记中心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该评分表由5个项目组成(总分10分):年龄、是否房颤、是否吞咽困难、性别(男性)、卒中严重程度(NIHSS评分)。若A2DS2评分≥4分,其预测SAP的敏感度为91%,特异度为57%;若A2DS2评分≥5分,其预测SAP的敏感度为83%,特异度为72%。这些阈值有助于识别需要严密监测或开始预防性抗菌药物治疗的高危患者[11]。
表1SAP风险预测评分表
3.2.2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预防性抗菌治疗(PANTHERIS)评分表:
PANTHERIS评分表由Harms等[15]于年在ActaNeurolScand杂志发表(表1)。数据来源为至年医院神经内科的例重症急性大脑中动脉梗死患者。该量表由4个大项组成(总分12分):年龄、意识障碍程度〔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WBC绝对值、入院24h内收缩压是否mmHg(1mmHg=0.kPa)。若PANTHERIS评分≥5分,其预测SAP的敏感度为78%,特异度为84%。该量表首次综合了SAP风险因素(如年龄和意识水平)、感染生物标志物(如白细胞增多)和交感神经过度激活标志物(入院24h内收缩压mmHg)。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如纳入样本量较小,未记录脑卒中严重程度,也未将明确的吞咽困难这一危险因素考虑其中等[15]。
3.2.3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相关性肺炎评分表(AIS-APS):
AIS-APS医院王拥军教授团队[47]于年在Stroke杂志发表(表1)。数据来源为年9月至8年8月中国国家卒中中心登记的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该量表评估8个方面(总分34分):年龄、病史或合并症(房颤、充血性心力衰竭、COPD、吸烟)、卒中前独立程度(mRS评分)、入院卒中严重程度(NIHSS评分)、意识障碍程度(GCS评分)、是否吞咽困难、卒中亚型(OCSP分型)、入院血糖。该量表的中位评分为8分,其预测SAP的敏感度为79%,特异度为77%。AIS-APS评分表中的评分项目全面,涵盖了SAP的主要危险因素。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一是研究纳入对象仅为住院患者,而在急诊室或入院短时间内死亡的患者以及在门诊接受治疗的脑卒中患者未包括在内;其二是仅适用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尚未包括出血性脑卒中患者[47]。
3.2.4 ISAN评分表(年龄、性别、卒中严重程度、卒中前独立程度):
ISAN评分表由Smith等[48]于年发表在JAmHeartAssoc杂志(表1)。数据来源为年1月至9月英国SSNAP数据库登记的例缺血性脑卒中或出血性脑卒中患者。该量表共包括年龄、性别、卒中严重程度(NIHSS评分)、卒中前独立程度(mRS评分)4项内容,总分22分。当ISAN评分为0分时,SAP的发病率为1.3%;当ISAN评分18分时,SAP的发病率上升至30%。此评分表适用于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患者SAP的预测,简单易行,入院时即可评估并进行危险分层(低危组:0~5分;中危组:6~10分;高危组:11~14分;极高危组:≥15分)。该评分表存在的不足之处:其一是由于基线数据不完整,SSNAP数据库近1/3的患者被排除在分析之外,这可能会低估SAP发病率;其二是对SAP的定义基于临床医生的诊断,而不是使用标准化的诊断标准[48]。
Kwon等[49]于6年在AmJInfectControl杂志发表的肺炎评分表和Chumbler等?[50]?于年在Neuroepidemiology杂志发表的临床评分系统量表,由于人群样本量小且仅为回顾性研究等,较上述量表缺乏通用性。
4 SAP的诊断目前SAP的诊断仍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制定的标准最为常用,约占75%[51]。年卒中肺炎共识小组推荐使用改良CDC肺炎临床诊断标准诊断SAP(表2)[52]。
表2卒中肺炎共识小组对SAP诊断的推荐意见[52]
5 SAP的预防和治疗5.1 预防方法:
古语曰"上医治未病",预防SAP发生是临床诊疗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脑卒中患者应加强基础护理,注意无菌操作、消毒隔离,防止交叉感染;同时应加强口腔护理,注意口腔清洁,对重症脑卒中患者可实施选择性口咽部净化或选择性消化道净化治疗。若病情允许,脑卒中患者行肠内营养时床头至少抬高30°~45°,并在鼻饲后半小时内保持半卧位,并定期监测胃内容物残留量。鼻胃管喂养时应注意检查患者鼻胃管的位置,避免鼻胃管错位,X线检查是"金标准"。对于误吸风险高的脑卒中患者最好采用幽门后置管(鼻空肠管)的方式进行喂养。
入院时对患者进行吞咽困难评估是预防SAP发生的极为重要的方法。给予吞咽困难的急性脑梗死患者建立常规的筛选流程对于有效降低吸入性肺炎的发生率非常有效,同时可根据情况适当行吞咽功能的康复治疗。对于应激性溃疡或应激性胃炎低风险的患者,应避免使用胃酸抑制剂。对急性脑卒中患者不推荐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如有条件,可对脑卒中患者进行流感疫苗、肺炎球菌疫苗等疫苗接种。ACEI可以抑制SP的降解,而SP是咳嗽反射的重要调控介质。但使用ACEI与SAP发生的关系目前尚不清楚。在日本老年脑卒中患者中发现,ACEI可以有效降低吸入性肺炎的发生率[53]。而一项多国家随机对照试验(RCT)的事后分析结果显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或有脑卒中史的患者,其肺炎发生率下降与使用ACEI无显著关系[54]。
5.2 治疗方法5.2.1 不推荐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
近期关于针对急性脑卒中后吞咽困难患者预防性抗菌治疗研究(STROKE-INF研究)[55]、卒中预防性抗菌药物研究(PASS研究)[56]的两项大型临床试验表明,预防性使用SAP经验性治疗的抗菌药物时,既不能降低肺炎的发生率,也不会改善脑卒中的预后。更为重要的发现是,两项研究结果均表明抗菌药物使用组与非预防性抗菌药物治疗对照组在严重不良事件、难辨梭状芽胞杆菌阳性腹泻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定植的发生率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一发现也是对"使用抗菌药物预防感染被认为是导致细菌抗菌药物耐药性的主要问题之一"的反证[55,56]。
5.2.2 有感染证据时抗菌药物使用策略:
广谱青霉素/β-内酰胺酶抑制剂的复合制剂是经验性治疗SAP的常用药物,重症患者可选择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入院后再根据病原学检查结果采取针对性治疗策略。
5.2.3 神经保护治疗5.2.3.1 抗交感/?HPA轴治疗和胆碱能抗炎通路:
研究证明,用β-受体阻滞剂普萘洛尔抑制SNS和用糖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米非司酮抑制HPA轴双重阻断,可显著减小脑卒中小鼠的脑梗死面积,改善长期存活并促进感染恢复[57]。
胆碱能抗炎途径主要包括迷走神经、nAChRα7以及脾脏[58]。活化的PNS分泌乙酰胆碱,而乙酰胆碱可抑制外周炎性细胞因子释放,发挥抗炎作用。nAChRα7的高亲和力激动剂伐伦克林延迟给药可减轻脑卒中小鼠的大脑炎症及改善其运动功能[59]。因此,改善胆碱能抗炎通路的策略为预防和治疗SAP提供了新的思路。
5.2.3.2 他汀类药物:
他汀类药物具有神经保护作用,可减少损伤,促进康复,预防脑卒中早期复发。因此,他汀类药物被认为对缺血性脑卒中的急性期有潜在的积极作用[60]。此外,辛伐他汀已被证明可以通过减轻脾脏萎缩和肺部细菌感染改善SIDS[61]。
5.2.3.3 亚低温治疗:
低体温可显著减小脑梗死面积,短暂的缺血区亚低温可通过减小梗死面积改善免疫抑制状态[62]。然而也有研究表明,低体温虽刺激T细胞释放抗炎细胞因子,在脑缺血区发挥神经保护作用,但可加重免疫抑制,增加感染易感性[63]。启动低体温时间窗、低体温持续时间和深度、间歇性还是持续性使用亚低温治疗、全身降温还是选择性头部降温、复温速度和复温终点温度均能影响免疫状态。因此亚低温治疗是否对SAP有益目前仍存在争议[64,65]。
5.2.3.4 干细胞疗法:
急性脑梗死的动物实验表明,干细胞治疗可减轻缺血后炎症损伤和改善动物的机体功能[66]。一些临床试验也提示脑卒中后的干细胞治疗(间充质干细胞、骨髓单个核细胞和神经干/祖细胞)是可行和安全的,但由于患者特征差异、治疗时机选择和干细胞类型与剂量不同,干细胞治疗效果一直存在争议[67]。
5.2.3.5 抗炎和免疫调节治疗: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靶向抗炎及调节免疫反应可能是挽救缺血脑组织和改善脑卒中预后的可行方法。一些特异性调节炎症或免疫通路的药物已经开始进行Ⅱ期或Ⅲ期临床试验,例如IL-1受体拮抗剂Anakinra、他汀类药物、芬戈莫德、西酞普兰、多奈哌齐、环孢霉素A、尿酸、纳他利珠单抗、人参皂苷-Rd、依达拉奉等[68]。动物实验表明,新型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caspase)抑制剂Q-VD-OPH可改善脑损伤,增强抗菌防御能力,减少实验性脑卒中后自发性细菌感染的发生[69]。
6 展 望SAP在临床上是脑卒中急性期常见的并发症。根据多中心的临床研究结果制定更能双重满足临床和科研的诊断标准,对于转化医学更有意义。预测SAP发生的临床评分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但为了临床实践中更优化地选择患者进行针对性管理,需要对危险因素进行细化分层,提出不同危险分层下不同的SAP预防和治疗策略。如何将SAP的治疗时间窗提前至脑卒中发生的超早期和明确增加SAP风险的药物,是目前临床和科研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对临床实际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优化SAP的抗菌药物治疗用药是全球"细菌耐药性"大环境下对临床医务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要求。针对急性脑卒中先天和获得性免疫功能受损,研制新型的免疫调节治疗药物可能是减少感染易感性的基础。有针对性地开发改善吞咽功能、上消化道运动的药物对预防SAP具有一定价值。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参考文献略)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soyingyong.net/yezqfy/7955.html
- 没有推荐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