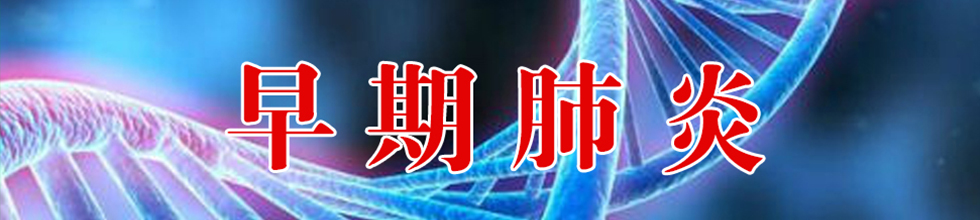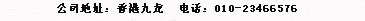基于文献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诊治思路的
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现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病例,并迅速爆发。在此次疫情中,中医药第一时间介入治疗,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疗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诊疗方案”从第三版开始纳入中医药诊治内容,并在其后各版本中加以不断改进。年2月6日,医院医院首批共计23例患者经中西医结合治疗后治愈出院,说明以中医药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确有疗效[1]。
目前国内抗疫工作虽然已经初见成效,但全球疫情仍不容忽视,境外输入性病例亦时有发现。如何总结经验,在下一步抗疫工作中进一步提高中医药的诊治效果,为以后出现的类似疫情时,中医药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理论依据,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目前中医药诊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思路进行分析、总结。
1.病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病名尚无统一认识。较早深入武汉疫情一线的仝小林院士提出本病当属“寒湿疫”[2],从之者众[3,4]。亦有认为本病属湿疫[5]、湿热疫[6]、湿毒疫[7,8]者。由国医大师张伯礼、王琦等主持编写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诊疗手册》则将本病属于“瘟疫”范畴,其病名可称之为“肺瘟”[9]。
《说文解字》言:“疫,民皆病疾也”[10]。《素问·刺法论篇》云:“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康熙字典》引《集韵》曰:“瘟,……疫也。”[11]可见,疫、瘟都是指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疾病,故而亦常二字并称曰“瘟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基本再生数(R0值)在疫情初期推测为2.2,之后上升至3.77[12],可见其传染性之强,归属于中医“瘟疫”范畴毫无疑义。出于文字表达习惯的不同,或称为“瘟”,或称为“疫”,均无不可。不同观点的区别,主要在于对本病特性的认识不同。认为其病以寒为特征者,称之为“寒疫”;认为以“湿”为主要特征者,则称之为“湿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表现的复杂性,常常可以表现出寒、湿、热、燥、毒等多种病邪特性,造成当前对其病名认识的混乱。因此,有学者将命名重心放在病位上,遂有“肺瘟”之名。
国医大师周仲瑛先生认为疫情之下,“战疫”如“救火”,“不必苛求什么具体的病因、病名。我们只要知道其属于中医温病中的瘟疫病范畴就可以了,病名不妨就暂借和西医的‘新冠肺炎’”[13],确有高明之处。检索当下发表的中医药抗疫的相关文献,无不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名之,可为周仲瑛先生观点之佐证。况且,无论辨为何疫,都不可能在概念上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建立完全对等的关系。因此,暂借西医病名,不但可以使中西医诊断标准一致,也更符合临床实际。
2.病因特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中医“瘟疫”病,其致病因素为“戾气”。吴又可《温疫论》指出:“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气也。戾气者,非寒、非暑、非暖、非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乃天地别有一种戾气。”[14]92([]内是引文序号的标示,[]后数字是该条文在书中的页码数)
2.1.“戾气”的致病特点
2.1.1.一气自成一病
“戾气”致病,具有一气自成一病的特点。不同的“戾气”可以导致不同的“瘟疫”,但同一种“戾气”所致之病,则病状类似。如《温病条辨》所云“温疫者,厉气流行,多兼秽浊,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15]这是“戾气”致病的独有特点,与脏腑、运气皆无关系。这种具有特异性的临床表现并不完全遵从于脏腑致病规律。以头面浮肿为特点的大头瘟,虽阳虚之人中之,亦有红肿焮痛;以下痢脓血为特点的疫痢,虽脾胃充盛之人中之,亦有下痢难禁。其致病更不局限于五运六气,“夫病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盖非五运六气所即定者,是知气之所至无时也。”[14]51
“戾气”中人,方始为病,则其临床表现也必然会受到病人体质、岁时运气的影响。吴又可于此特别指出“殊不知四时之气,虽损益于其间,及其所感之病,终不离其本源。”戾气自身的致病特点为其“本源”,四时之气,则“损益于其间”,对患者的具体见症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故而“四时皆有暴寒,但冬时感严寒杀厉之气,名伤寒,为病最重,其余三时寒微,为病亦微。”[14]94
2.1.2.多兼秽浊之气
许多学者在此次战疫中观察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兼有秽浊的临床特点,他们多半将其与湿邪联系起来。这当然是有道理的。湿性重浊,常常表现出秽浊的症状特点。清代石寿棠《温病合编》云“温疫者,温盛为疫,乃湿土中郁蒸之气,多兼秽浊……”[16]16。实际上易兼秽浊正是“戾气”致病的固有特点之一。吴鞠通《温病条辨》云:“厉气流行,多兼秽浊。”[15]“风火暑三者为阳邪,与秽浊异气相参,则为温疠”[15]。因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湿热表现,可能只是戾气所兼之秽浊之气。其形成既可能与武汉地区去冬潮湿多雨有关,也可能是患者本有内湿,遇温热阳邪相合而成,或者是戾气中人之后,脏腑功能失调所致[13]。
2.1.3.疫多挟毒热
古来“瘟”、“疫”并称者,疫病多挟毒热之故也。余师愚在《疫疹一得》中提出“疫疹乃无形之毒”[17]序,“瘟既曰毒,其为火也明矣。”[17]24疫戾之气致病,常挟热毒为患,热毒为阳邪,其性鸱张善变,故而不但病势急迫,而且传染亦速,而成一方之疾。因此之故,王孟英认为“疫证皆属热毒,不过有微甚之分耳。……或热邪不重,过服寒凉,亦宜温补回春,然非疫疠正治之法。”[18]
2.2.新型冠状病毒的致病特点
既然借西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名来讨论此次疫情,则需要对其病原体“新型冠状病毒”(下文简称“新冠病毒”)的致病特点做一个中医解读。基于“新冠病毒”的强烈传染性,其属中医之“戾气”当无疑问。因此,也就必然具备戾气的特点。虽然“戾气”不同于六淫之气,但除了具有强烈传染性之外,其致病的临床特点总不出六气范畴,这是由中医认识世界的固有范式所决定的。仔细研究“新冠”致病的六气特点,是能够准确施治的前题,此即《素问·至真要大论》“审察病机,无失气宜”之意。
清·钱潢在《伤寒溯源集》中云“外邪之感,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19]审证求因是分析“新冠”六气特点的唯一方法。疾病初起,未经治疗,受患者体质影响也较小,此时的临床表现最能反映新冠病毒的致病特点。
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明确指出本病初起“以发热、干咳、乏力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肌痛和腹泻症状。中国学者在疫情前期发表于柳叶刀的研究也表明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83%),咳嗽(82%)、气促(31%)和肌肉疼痛(11%)[20]。乏力并不是一个具有辨证特异性的症状,虚、实、寒、热等各种病机都可以引起患者有明显的乏力感。因此,不能将乏力做为判断“新型冠状病毒”致病特点的依据。
中医视角下的发热,并不只着眼于患者的体温变化,其发热特点和兼证对于判断病邪特点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发热症状多表现为身微发热、身热不扬、午后身热、夜间潮热,而壮热较少,部分患者还表现有手足心热、日晡潮热和寒热往来[21]。而多数患者初起发热的热度并不高,表现出身热不扬的特点[22]。除了夜间潮热之外,上述发热症状显然符合湿热的发病特点。湿阻气机,热邪不能透发,所以微发热,身热不扬。“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午后为末时至酉时,日晡为申时,皆为阳明主时。阳明属土,故而湿温发热,多以午后、日晡为甚。湿热之邪由口鼻而入,留于膜原半表半里,故而可见寒热往来。脾主四肢,手足心为四肢末端,湿热留连脾胃,热气熏蒸,旁达四肢,则见手足心热。
对干咳的理解争议较多。有认为是寒湿阻肺者[2],有认为是伏燥[2]者。若以燥邪来解释干咳,则本病口干咽燥等燥证见症并不多见,症机颇有不符。如果是寒湿闭郁肺气,则寒水互化,多以咳喘痰稀,或咳出清稀水饮为特征,与本病的临床特征明显不符。肺气闭郁不宣,确实可见干咳。跟据尸检结果,死者肺中大量痰液,因此干咳并非燥邪所伤,而是痰湿闭郁不出[23]。有报道称,在辟秽解毒、分消走泄、养阴和营治疗后,病人由干咳转见痰量明显增多。随着痰量的增加,喘憋气促逐渐好转,病情向愈[24]。这也说明病人的干咳并非津液不足,而是痰湿的闭郁。痰湿的来源,则是疫毒阻滞气机,津液不化[25],失于布散,积于肺中,化生而来。
辨别病邪性质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舌脉。多数研究者观察到的舌象都比较类似,舌体红或淡红,尖部明显,舌苔以厚/腻苔多见[26,27]。脉象则以滑脉、数脉为主[28]。舌红苔腻脉滑是湿热证的典型表现,也可以解释为秽毒之邪为患。秽毒本来就是戾气自身最常兼见的属性。以六气的角度来分析秽毒,秽则类湿,毒为热盛,秽毒相合,颇类湿热。新冠戾气的这一特点使得它极易与湿温混淆。但是湿温病常发病较缓、传变较慢、病程较长,流连气分,多袭脾胃,以长夏之时最为常见。本次疫情发于冬日,病位在肺,一旦发病,传变迅速,与湿温病大有区别。因此,与其说新冠病毒有湿热之性,不如说以其为乖戾之气,性挟秽毒,具有与湿热类似的临床表现更为合适[13]。本次新冠肺炎患者早期表现出的纳呆、便溏,口干不欲饮等典型湿热见症,则不能单以秽毒来论,而是新冠戾气独有的致病特点。
戾气虽为天地杂气,然其致病亦受四时之气的影响。病发于冬者,常兼寒邪;病发于夏者,则兼暑热。本次疫情起于晚冬,适为寒气主令,故而初起可兼寒象。这种四时之气的影响也与地域有关。天气更为寒冷,且无室内供暖的襄阳地区,寒湿之象较为明显[29]。而同一时期,在南方温暖之地的江苏[30]、上海[31]等地区,则并无寒象,只以湿、毒为主要特征。这也说明,“寒”并非新冠戾气的固有特点。
综上所述,新型冠状病毒属于中医戾气,可以称之为“新冠戾气”。其致病特点为秽浊毒盛,临床特征以湿、热为主,可随时间、地域而兼具其它六气的致病特征。
3.病机演变及治疗
3.1.病机演变
新冠戾气由口鼻而入,首先犯肺,易困脾阳。以其具有湿、热的致病特点,所以多数患者按薛雪《湿热论》的正局演变,由肺表入膜原,再渐次深入,留于三焦。经正气抗邪,或治以三焦分泄,邪气渐去而向愈。但疫病传变,最是复杂,《温疫论》有九传之说[14]83。故而新冠传变并不完全拘于湿温正局、变局,而是极易入里,引起病情的迅速进展。重症患者多在发病一周后出现呼吸困难和/或低氧血症,严重者可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及多器官衰竭等。
重证和危重证患者的主要症状是喘促憋闷。尸检结果显示患者肺脏呈不同程度的实变。肺泡腔内见浆液、纤维蛋白性渗出物及透明膜形成。这种类似于中医“痰湿”的病理产物是重证阶段肺气闭阻的重要因素。痰湿闭阻中上二焦,气机闷瞀不通,初起尚可急用辛开苦降,分消走泄。针对新冠病情进展中以痰湿闭阻为核心的特点,可以在初起之时,即注意阻断痰湿的形成[32]。比如及早采用宣肺化湿,芳香避秽的方法,使气机宣散,津液布化,而不生痰浊。痰浊既成,则宜尽快袪痰开泄。若待顽痰已成,积于胸膈之间,脉络深处,则化之不及,祛之难出。在内闭阻气机,在外耗气伤津,而成内闭外脱之证。
3.2.分期治疗
湿疫病常表现出相对固定的病情演变规律,因此可以在总结病情规律的前题下分期论治。新冠诊疗方案第七版将本病分为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恢复期五个阶段。轻型和多数普通型其实是病情发展初期,病变特点类似,只是轻重程度有所不同。因此,从病情发展规律上看,可以简化成初期、进展期、极期和恢复期。
3.2.1.初期宜辛凉开泄
疫气伤人,直入膜原,初起即可见发热、乏力、身痛等症。而新冠戾气则尤易伤肺,郁闭气机,而见干咳、咽痛。此时邪未深入,可予达原饮分消走泄,或合以银翘散辛凉透表,宣散肺气。若热毒盛者,甘露消毒丹亦可以用之。
3.2.2.进展期宜辛开逐邪
若疫气未能从膜原而解,反而化热入里,湿毒闭阻肺气,而见发热面红,喘憋气促,痰少难出,口干苦而粘之重证。则应辛开胸膈,通畅肺气,通利肠腑,以逐疫邪。辛开胸膈,可仿薛生白治湿热阻闭中上二焦之法,以草果、槟榔、鲜菖蒲、栝蒌、栀子、淡豆豉、六一散重用之。或用《温病条辨》杏仁滑石汤亦可。通利肠腑则可合用升降散。肺气闭郁较甚者,葶苈大枣泻肺汤亦可随证加入。
3.2.3.极期宜回阳救阴,开窍启闭
若疫气未得及时驱逐,则深踞胸膈肺络。肺气不宣则喘憋欲绝;津液不化则顽痰深伏;毒热入营则高热神昏,甚至谵语;疫毒伐伤,则阴阳俱虚。此时疫毒之邪不减反盛,正气却耗伤太半。治疗重点要先在正气上,以求“留人治病”。疫毒之邪,其性本热,易伤阴津,故而极期患者,多有亡阴之虑。此期患者舌象多为舌暗红,苔浊腻或黄腻。有报道中西医结合治疗6例重型及危重型患者,所见皆为红舌[33]。可见极期伤阴者多,伤阳者少。宜大补阴液,以存津液。可仿薛生白治湿热劫津,木火犯胃法,重用生地汁,西瓜白汁[34]54等养阴增液之品,亦可加用二冬、洋参、石槲之类。尝见仝小林院士救治某重型患者,以生脉散加味,西洋参代人参,重用麦冬至45克,生地至30克,三剂而诸症大减。或有以阳气脱失为主的,则宜用参附四逆汤之类以回阳救逆。
扶正的同时,也要积极开窍启闭,以救气机。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皆可随证选用[35]。考虑到新冠极期痰热闭阻的特点,至宝丹当尤为适宜。
3.2.4.恢复期宜益气养阴,轻清宣透。
《温疫论》有云:“夫疫乃热病也,……阴血每为热搏,暴解之后,余焰尚在,阴血未复”[14]27。新冠戾气多挟秽浊毒邪,兼具湿邪特性。热伤津液,湿阻阳气,故而恢复期当以阴虚邪恋为基本病机,或可兼见阳气不足。本病以肺为主要病位,兼及脾胃。所以阴虚则多肺胃津伤,气虚则多肺脾不足,余邪留恋则常以湿热蒙绕为特征。各地对恢复期临床表现的观察符合这一理论推测。
数据显示,恢复期发生率最高的症状依次为小便短黄、口渴、汗出、口苦、乏力、胸闷气短、大便不畅、心烦不寐、身热夜甚和咳嗽咳痰,以红舌或黯红舌,腻苔为最多[36]。主要证型包括肺脾不足,气阴两虚和无明显证状类[37]。国医大师熊继柏也认为恢复期以脾肺气虚或肺胃津亏最为常见[38]。肺脾不足者,可治以黄芪六君子汤[38];气阴两虚可治以竹叶石膏汤合沙参麦冬汤[39];肺胃阴虚可治以沙参麦冬汤[22];余邪未尽可治以五叶芦根汤[35]。由于新冠肺炎常表现为病情迁延,反复多变的特点,恢复期各种证型均可以辨证基础上予五叶芦根汤加减,以防“炉烟虽熄,灰中有火”[34]17。
4.对几个疑问的思考
4.1.麻黄是否可以使用
对国家及各地卫生主管部门发布的中医药防治COVID-方案的方证规律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发现初期用药中以辛温解表药如麻黄等的使用为多[40],也有一些中医大家提出在治疗过程中一定要善用麻黄[41]。
但本次新冠肺炎是由戾气所致的疫病,挟秽毒之气而具湿浊之性。吴又可《温疫论》云:“此邪热浮越于经,不可认为伤寒表证,辄用麻黄桂枝之类强发其汗。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表气,热亦不减”[14]4,力戒治疗疫证时轻用麻黄。戾气致病,与伤寒不同,由口鼻而入之后,往往直入膜原。邪气既不在表,麻黄之辛温不但难以祛邪外出,反而因其发散,引起毒热邪气加重病情[35]。而在疫毒闭肺阶段,痰热疫气搏结于胸膈肺脏,亦非麻黄之表散所能开宣。因此,也有不少医家提出本病治疗,不宜使用麻黄[13,35,42]。
从本次新冠肺炎救治的实践来看,麻黄是得以大量使用的。例如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的通用处方“清肺排毒汤”,广泛用于新冠肺炎的轻型、普通型、重型及部分危重型患者,能显著改善患者的发热、咳嗽、气喘、乏力等临床症状,阻止病情加重[43]。方中即有麻黄,并与桂枝同用。医院西院观察“清肺排毒汤”治疗例新冠患者,有56例(16.57%)患者汗出增多,均诉适量汗出后气短胸闷有所缓解。仅有2例(0.59%)汗出过多。而在严格去沫处理后,这些不良反应也明显减少[44]。说明在新冠治疗中,适时、适量使用麻黄是有助于治疗的,更非禁忌之症。
实践与经典温病理论之相左,正是理论创新的契机所在。麻黄究竟是必用之药,还是禁用之品;如非禁忌,则又当如何据证使用?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中医理论。
4.2.危重证是否可以使用劫痰法
尸体解剖结果显示,肺组织的渗出、黏液、肺水肿是新冠致死的重要原因。可见痰湿为患是伴随新冠病情进展的主要病机之一,疾病后期顽痰闭阻肺络,是导致阴阳离绝的重要原因。疫病治疗以袪邪外出为第一要义,于此秽毒所生之顽痰,若不及时加以袪除,而只是将治疗重点放在扶阳救阴上,可能难以逆转病情。
对于这种胶粘难出的顽痰,中医素有逐痰、劫痰之法。在疾病进展期就及时应用,逐痰外出,可能是阻断病情进展的关键。故而有学者提出早期应宣肺化湿透邪;中期宜化痰清热利湿;晚期仍应祛痰化瘀,扶助元气,将化痰法贯穿新冠治疗全程[32]。分析文献,所选化痰药物多以陈皮、半夏、杏仁、葶苈、桑白皮、瓜蒌皮、桔梗、紫苑、款冬之类,经典逐痰药如白矾、皂角、礞石、泽漆等均未见使用者。
以逐痰法开宣上焦气机,《湿热论》中即有论述。其第十四条“十四湿热证,初起,即胸闷、不知人、瞀乱大叫痛,湿热阻闭中上二焦。宜草果、槟榔、鲜菖蒲、芫荽、六一散,各重用。或加皂角,地浆水煎。”[34]54重用草果、鲜菖蒲之类辛开湿郁是为常法,加皂角是为了加强清化痰热的力量,以开闭阻之气机。在新冠的治疗过程是否可以据证使用这些力量较强的逐痰药,甚至如控涎丹、礞石滚痰丸等袪痰重剂?其使用时机和力度又当如何把握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这可能是提高中医治疗极期重症成功率的一个切入点。
5.小结
新冠肺炎属于中医“瘟疫”病范畴。其致病因素为戾气,可以称之为新冠戾气。其致病特点为秽浊毒盛,临床特征以湿、热为主,可随时间、地域而兼具其它六气的致病特征。新冠戾气中人,多由口鼻而入,首先犯肺,兼及脾胃。极易入里,形成重证和危重证。可以根据病情的不同发展阶段分期论治。治疗过程中要始终以袪除戾疬毒邪为第一要务,初期可以辛凉开泄,进展期宜辛开逐邪,极期宜回阳救阴、开窍启闭,恢复期在益气养阴以复正气的同时,还要重视轻清宣透,以除余邪。
References
[1]人民网.医院18名确诊患者治愈出院[EB/OL].(-02-06)[-02-06].
转载请注明:http://www.soyingyong.net/yezqfy/6547.html
- 没有推荐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