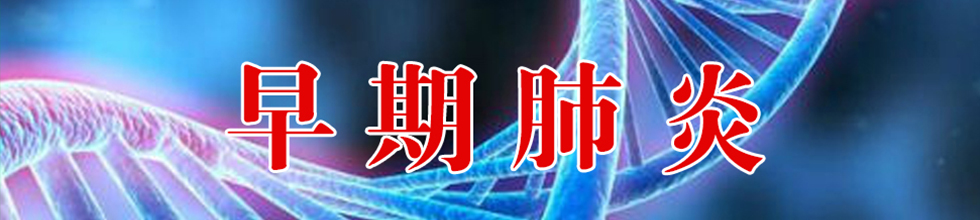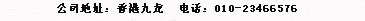从脾湿肺燥论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从脾湿肺燥论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姜昕1庞立健2吕晓东1
王佳然1车艳娇1荆莹1
(1.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沈阳;2.辽医院,辽宁沈阳)
摘要: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治,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文主要从脾湿肺燥出发论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审证求因,认为其因外感"湿毒夹燥"性的疫疠之邪而致;病机特点为毒、湿、燥、虚,以"湿"为核心;初起病位在脾、肺,后期亦可牵连它脏。从肺脾功能及燥湿特性方面阐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脾湿肺燥证成因;由此归纳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脾湿肺燥证治疗思路,以健运脾胃为治疗之根基,以燥脾湿、泻脾热为治疗之关键,以润肺燥、滋肺阴为治疗之核心。以期为预防、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湿毒夹燥;脾湿肺燥
近年来,中医药在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治疗中利用其独特优势,发挥了良好的防治作用[1,2,3]。本文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例,从脾湿肺燥出发,探讨中医药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治作用,以期为临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治提供理论参考。
1背景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属急性传染性疾病,主要是由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引起,具有传染性强[4]、家族聚集现象[5]、普遍易感等特点。针对感染者数量增加、多个国家均出现疫情、患者首发症状与病情程度各不相同这些事实,以此认为本病的治疗方案不能一味的墨守成规,而应在常规抗病毒治疗的基础上配合中医特殊的治疗方法,各取所长,中西并重[6],以共克疫情。目前,现代医学对于本病主要采取隔离、对症及支持疗法。而中医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以整体观念为切入点,对疾病进行辨证以确定具体的治疗方案。对于疫情,各地纷纷出台措施,充分发挥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中医力量,且均证明中医药对疫情救治工作有效[7,8]。
古人认为温疫的病因是感染疫毒之气,此疫毒具有季节性发病的特点;戾气通过口鼻侵犯人体,其传播性与致病力较强,易出现家族聚集现象,且病势危急。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因、流行病学特点及症状表现,将其归属于“疫病”范畴[9]。但根据其发病的时令及地理环境等因素,将其具体划分于“寒湿疫”范畴中[10]。
2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病因、病机、病性、病位
2.1发病因素
2.1.1外感疫疠之邪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病的外因为感染疫疠之邪,确切说是外感“湿毒夹燥”性的疫疠之邪。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认为瘟疫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三国时期,曹植认为疠气是由“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隋朝时期,巢元方认为疫疠病与“节气不和”有关。以此得知,气候不相宜,可滋生戾气而导致疫疠病。“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阐述了戾气病邪传染性强、易于流行的特点,此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致病特点相似,故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因感染疫疠之邪而致。辨证求因发现,本病患者多具有发热、乏力、倦怠、身热不扬等临床表现,少数患者以腹泻为首发症状,以此考虑本病与“湿邪”有关;部分患者还具有明显干咳等症状,考虑本病亦与“燥邪”有关;因此,可以将湿、燥二邪认为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致病原因。综上,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主要是外感“湿毒夹燥”性的疫疠之邪而致。
2.1.2内则正气不足
疾病的发生除邪气影响外,正气也起着决定性作用。正气旺盛,则可规避邪气,以不致发病,故“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正虚可以感邪而发病,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内在根据,外因通过内因以侵犯人体。若机体正气衰惫,卫外不固,邪气趁虚而入,或感邪较重,毒性较强,邪盛而正衰,抗邪无力,因而导致机体阴阳消长失于平衡、脏腑功能失调、气机逆乱而致病。病邪愈盛,毒力愈强,机体生理功能衰惫,病情趋向恶化,危重者则阴阳离决。故正气虚弱者,易被传染而发病。故谓“邪胜正负而发病”。
2.2发病病机
本病是因机体正气相对虚弱[11],而又外感“湿毒夹燥”性的疫疠之邪,邪胜而正负,机体抗邪无力而暴发。疫毒邪气由外入里,经口鼻而入以侵犯机体,正负邪胜,阴阳失调,故见发热;若湿遏热伏,则见低热。湿邪侵入机体,易影响气机运行,而阻滞气机,作用于中焦,则见胸闷。且湿性重着,故病之初始阶段必兼沉重感,或头重,或肢体困重。“太阴湿土,得阳始运”,欲求干燥而恶湿,湿性属阴,易损阳气,尤以损伤脾阳为主,脾阳虚衰,失于温运则见腹泻;气血不足则见倦怠乏力。肺为清虚之脏,燥邪上犯肺经,肺津亏损,则见干咳。戾气袭肺,宣降失职,重者可见胸闷或呼吸困难。且戾气致病起病急剧,变化莫测,病势危急,致病过程中易伤津耗血、攻心,出现危重症候。若失治、误治,则湿毒化热[12],肺病逆传心包,心主血属营,易可出现神昏等内闭外脱之证[13,14,15]。综上,可将本病病机特点归纳为毒、湿、燥、虚,以“湿”为核心[16,17]。本病发生亦是由实转虚的过程,起病急剧,变化莫测,传染性强,因失治、误治,亦或病情迁延,邪气虽然渐去,但机体正气或是脏腑功能受到严重损伤,病机由实转虚。
2.3发病病性
本病以脾湿为主,湿郁化燥,湿盛伤脾,脾虚反而生湿,故以脾肺虚为本,以湿盛为标,属本虚标实。结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症状表现,可以判断出本病初期以“湿”为主[18],属实性病变。湿为有形之邪,其性沉重,易影响气血运行,从而阻滞气机。湿困脾胃,升降不利,纳运失调,影响脾的运化功能,津液困阻于内,不得布散,进而内生湿浊,则属标实。湿性黏滞,致使病程缠绵。湿邪郁久,以致邪郁化火,火热消灼阴津,致使体内津液不足,津伤化燥,燥而伤肺,此时湿燥相兼,则属本虚标实。病邪愈盛,毒力愈强,机体生理功能衰惫,邪胜而正负,病情趋向恶化,则出现以正气衰惫为主的虚性病理变化,此时则属本虚。
2.4发病病位
湿通脾,燥通肺,“湿毒夹燥”其在五脏上则表现为脾湿肺燥证[19],故本病初期以脾肺二脏病变为主,后期亦可牵连它脏。
湿邪外感,益困于脾;而湿浊内生,多因脾失健运所致。脾气不足,运化失职,卫气缺乏化生之源,对外则不足抵抗邪气侵袭。脾气受伤,生化之源匮乏,全身脏腑功能低下,而见神疲乏力、少气懒言等羸弱症状,抗病力弱,致使疾病缠绵难愈。外感湿邪困遏脾阳,亦或饮食所伤、脾胃虚弱等因素,影响脾胃运化功能,致使脾胃传导失司,升降失调,而导致腹泻。湿盛则脾虚,反之脾虚亦可生湿。湿盛伤脾,脾虚不运而生湿,脾虚与湿盛两者相互转化,合而为病。脾胃一伤,百病丛生,脾病亦可导致其他脏腑病变。
肺在体内脏腑中位置最高,而主气司呼吸,朝百脉主治节,宗气及津液、水谷精微的输布布散,皆依赖于肺的呼吸及宣降作用,故肺为脏之长,覆盖诸脏,以抵御外邪。盖以气通于鼻,鼻作为气体出入的通道,与肺直接相连。疫邪通过口鼻侵犯人体,肺脏清虚不耐邪侵,且为华盖,故最先、最易受损。“肺被燥伤则必咳嗽”,燥胜则干,外感燥邪或内伤火热,伤及肺脏,损伤肺阴,肺失宣肃,则见干咳无痰。
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脾湿肺燥证成因
3.1肺脾功能相关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脾湿肺燥证形成的生理基础
肺脾功能相关表现在气的生成与水液输布方面[20]。人体需依赖脾的运化功能,以消化饮食,吸收水谷精微并将精微物质转输全身,从而发挥滋养作用,以枢转水液,调节水液代谢,防止水液停滞而生湿。脾将精微升输于肺,以化生气血,充养全身。土生金,土能滋生、滋长金,故脾能助肺益气。脾在发挥运化功能的同时,需要肺的宣降功能为辅,方可将津液敷布全身。肺主气,人身之气均为肺所主,且肺可调节治理气血津液输布运行,以保证机体阴阳平衡,气血健旺。人体内水液输布亦与肺密切相关,肺主行水,通调水道,调节全身水液的输布排泄,以防止体内水液潴留。肺、脾协调为宗气生成的基础,宗气的形成不仅依赖于肺的呼吸功能,还依赖于脾的运化功能,宗气生成充足,则一身之气充沛。
脾胃受损,气血不足,机体防御功能减弱,易感邪侵。脾虚不运,水液失于布散积聚体内而生湿。湿邪留滞体内,日久郁结不祛,以致郁而化燥,燥则伤肺。肺气虚损,宣肃无力,水液输布失常,聚而成湿,以伤脾。脾气亏虚,运化失职,水谷不化,则见腹泻、肢体倦怠。脾升输无力,不能上输水谷精微,肺失所养,则影响肺的功能。如此循环反复,以致肺脾皆虚。脾土为母,肺金为子,始而母病及子,继以子病及母,脾湿能引起肺燥,肺燥亦可导致脾湿的形成,而致脾湿、肺燥两者均盛,最终形成脾湿肺燥证。
3.2燥湿特性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脾湿肺燥证形成的病机基础
湿邪有质而无形,其性重着,易停滞脏腑、留滞经脉,从而影响气机升降,机体也因此出现沉重感。湿遏清阳,则见头痛;湿遏胸膈,则见胸闷。且湿为阴邪,阴盛则阳衰,湿邪入侵机体尤以损伤脾阳为著。“湿胜则泄”,脾阳虚衰,失于温运,则见泄泻,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少数患者伴有腹泻症状。脾气不足,除了有便溏等脾病表现外,亦有乏力、倦怠等气虚表现,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以乏力为主要表现。湿邪致病黏腻弥漫,蕴蒸不化,胶着难解,表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起病较缓隐匿、病程较长的特点。
燥气太过则干燥少津,燥为干涩乏津之证。燥易伤津,且易伤肺。因肺与鼻相通,外感燥邪可直接伤及肺脏,损伤津液,而致肺宣降失职,出现干咳少痰、喘息胸痛等表现。湿郁日久不祛亦可化燥形成内燥。湿邪偏重,日久不祛,体内郁积,则阻滞气机,郁而化热,热灼津液,津伤而化燥,燥则伤肺。脾欲求干燥清爽,而肺的生理特性却与脾截然相反,肺脏娇嫩而性喜清润。脾湿能引起肺燥,肺燥亦可导致脾湿的形成,而致脾湿、肺燥两者均盛。
3.3内外合邪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脾湿肺燥证形成的重要机制
“夫病固疾,加以卒病”,其实质上说的就是因内外合邪而致病。饮食失节及体质因素,可伤及脾胃,脾虚不运,水液聚集停滞,而内生湿浊。机体易外感湿邪侵袭,湿易伤脾,则脾运失健。本病素有正气不足的内因,机体无力抗邪,即抵御湿邪的功能低下,从而导致外界湿邪则易内犯。湿郁化热,热胜伤津,津伤而化燥,内燥病变,易伤及肺脏,以致肺气虚弱。内有伏邪,机体正气不足,或原本失调,其御邪抗病能力必然下降,燥气盛行,以致外燥犯肺。
简而言之,内生之邪常为外感邪气的内应,内有伏着之邪,是招致外邪侵袭的重要因素。内外合邪,邪结不解,合而伤人,其势归一,正邪交争必伤正气。正气不足,外邪易于侵入,内损脏腑,从而内生病变。内伤病因直接损伤脏腑,导致体内阴阳失衡,机体抗病力弱,感邪即发。本病以“湿”为核心病机,外感湿邪常易困脾,内生湿浊多因脾失健运而致;外湿日久亦可导致内湿的形成,内湿则脾虚,机体易感邪气,又可引起外湿,两者互为因果。内湿则脾虚,脾阳虚损,水湿不化,容易外感湿邪[21];外感湿邪,多伤脾胃,脾不运湿,则滋生内湿。湿郁化热,热胜伤津,津伤而化燥,内燥病变,易伤及肺脏,以致肺气虚弱,外感燥邪且易伤及肺脏。湿燥为对立的两方面,湿燥相兼,故内外合邪是脾湿肺燥证形成的重要机制。
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脾湿肺燥证治疗思路
4.1健运脾胃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根基
“治病必求其本”,脾虚失运是致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生的内在因素,故健运脾胃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根基。脾胃健运,一方面水谷精微化生充足,气血充盛,从而转输全身,脏腑得以滋润;另一方面枢转水液,脏腑组织得以濡养,水液代谢输布正常,可防止水湿的形成。脾胃健运,气血协调,营卫调和,以防御外邪[22]。中医针对虚证的治疗上,不仅强调“虚者受补则生”,而且还重视“虚者补其母”的作用。肺虚的病人,除常规补肺外;还可补脾益肺,通过“培土生金”,以恢复肺脏功能。肺脾协调,诸气生成有源,则一身之气充沛;肺脾协调,亦可促进津液代谢,以防痰湿的形成。治病求本,疾病治疗时应根据疾病根本原因以确定正确的治本方法,故本病以运脾为治疗之根基。
4.2燥脾湿、泻脾热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关键
“湿”贯穿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展的全过程,“湿者,太阴土气之所化也。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人为脾”,所以无论是外湿,还是内湿,均依附于脾脏,故湿病治疗之根本在于治脾,以燥脾湿。湿盛阳郁,发而为热,湿易化热,故早治疗,以泻脾热。综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病病因病机及脾湿肺燥证的成因,可以得出,脾湿为本病的核心。湿阻中焦,脾运失职,升降失调,清浊不分,则见腹泄[23]。脾虚而生内湿,湿犯上焦则影响肺脏功能,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肺脾二脏病变为主。脾恶湿,燥湿所以健脾。湿浊困脾,郁久不化,阻遏气机,湿盛而阳郁,火盛则湿化为热,故治疗时以泻脾热。“湿热者,治以燥凉”,故燥脾湿、泻脾热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关键。
4.3润肺燥、滋肺阴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核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核心病位在肺。肺脏清虚而苦温燥,不耐邪侵,燥邪外袭,易直接犯肺;湿郁化火,耗灼阴津,阴津亏损,燥热内生,燥则伤肺。燥热灼肺,阴津亏损,无法生水,肺失所润,以致肺阴亏损。肺阴不足,阴虚阳无所制,火热燔灼趋上,煎熬津液,肺失滋养而致肺燥。“燥”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生的病理因素;新冠患者有干咳的表现,就是因为燥气侵犯于肺,肺失清降而引起的,“咳而无痰者,宜以辛甘润其肺也”。且“湿”亦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要的病理因素,湿郁之极,必兼燥化,故治疗时要润肺燥。肺阴亏损,虚火亢旺,虽灼液成痰,但胶着难咯,故见干咳无痰[24],因此治疗时应滋肺阴。故润肺燥、滋肺阴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的核心。
5小结
对于本病审证求因,认为本病以“湿”为核心,且兼夹“燥”的特征,故以脾湿肺燥为本病主证。“万物以土为母,而人身亦然……有脾土而后生肺金”,脾胃为后天之本,是人生存的根本,“然调脾胃者,其人昌”,中医强调固护脾胃以治未病;脾胃调和,则气血充沛。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性强、病情缠绵,故要早期诊治,以治未病。且本次疫情具有燥性特征,为湿毒夹燥性疫邪,病位在脾肺,故治疗时以健运脾胃为治疗之根基;以燥脾湿、泻脾热为治疗之关键;以润肺燥、滋肺阴为治疗之核心。总之,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展的各阶段,中医药皆可发挥一定的作用。希望本文可以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马钦海,邢学锋,罗佳波.清热解毒类中药抗呼吸道病毒研究进展[J].广东药学院学报,,32(5):-.
[2]朱家勇,朱盛山.中医药在防治非典中的作用[J].广东药学院学报,,19(3):-.
[3]YANDX,YUXP,SHIKH,etal.Discussionabouttreatmentof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basedonsyndromedifferentiation[J].JournalofIntegrativeMedicine,,2(4):-.
[4]LIQ,GUANX,WUP,etal.EarlytransmissiondynamicsinWuhan,China,ofnovelcoronavirus-infectedpneumonia[J].NEnglJMed,,(13):-.
[5]HUANGC,WANGY,LIX,etal.ClinicalfeaturesofpatientsinfectedwithnovelcoronavirusinWuhan,China[J].Lancet,,():-.
[6]滕俊,姜云宁,柴欣楼,等.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研究进展[J].中医学报,,35(4):-.
[7]徐旭,张莹,李新,等.各地区中医药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方案分析[J].中草药,,51(4):-.
[8]蒋鹏飞,李书楠,刘培,等.全国各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防治方案分析[J].中医学报,,35(4):-.
[9]严光俊,李洁,颜晓蓉,等.荆州地区普通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证候分布规律研究[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2(5):1-4.
[10]李董男.“扶正祛邪”辨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思路[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2(5):41-45.
[11]郑立夫,郑碧云,唐纯志.从脏腑致病角度分析导引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中的应用[J].中医学报,,35(5):-.
[12]郑一,郭鹤,于游,等.基于“肺-脾-大肠”相关理论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证候病机[J].中华中医药学刊,,38(4):1-3.
[13]窦晓鑫,杨玉莹,卜志超,等.试从中医角度认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J].天津中医药,,37(2):-.
[14]潘芳,庞博,梁腾霄,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防治思路探讨[J].北京中医药,,39(2):-.
[15]仕丽,刘继民,牛崇阳,等.王檀教授从气化顿滞论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J].吉林中医药,,40(4):-.
[16]于明坤,柴倩云,梁昌昊,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预防及诊疗方案汇总分析[J].中医杂志,,61(5):-.
[17]苏凤哲,李敏,王培,等.论痰湿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病中的作用及对策[J].中医临床研究,,12(6):68-70.
[18]丁瑞丛,王峰,陆虎,等.从脾胃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诊治[J].中医学报,,35(4):-.
[19]范伏元,樊新荣,王莘智,等.从“湿毒夹燥”谈湖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特点及防治[J].中医杂志,,61(7):-.
[20]陈东杰.参苓白术散加减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证属肺脾气虚型的中医证候疗效观察[D].武汉:湖北中医药大学,.
[21]刘芳芳.基于差异蛋白组学对外湿环境下脾阳虚大鼠的发病机制研究[D].武汉:湖北中医药大学,.
[22]罗秋燕.小儿治未病应从调理脾胃入手[J].世界中医药,,7(3):-.
[23]陈小洪.泄泻的中医证治规律研究[D].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
[24]周婧媛,韩新民.《小儿药证直诀》对肺炎喘嗽诊治的启示[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42(8):-,.
编辑:邹吉宇
校审:王佳然
总校审:于睿智
吕门优选打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soyingyong.net/fyzqzz/8463.html
- 没有推荐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