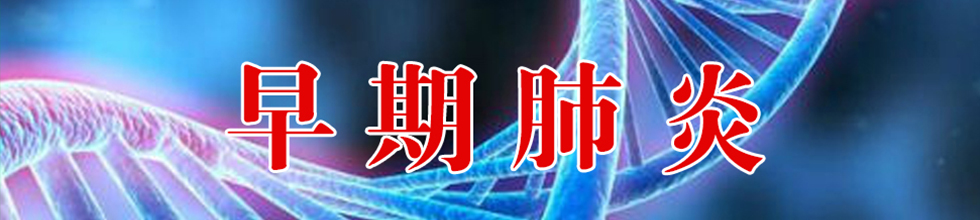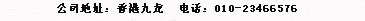近代日本的世界观日本如何向外国学习专访石
徐悦东我们经常说日本人善于向外来者学习,这个印象是如何形成的?如何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解释日本人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而且,日本人在吸收外来文化中,又如何形成日本自己的意识?在中日近千年的交往当中,日本何以形成它们独特的文化?在明治维新中,兰学又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日本史研究专家马里乌斯·詹森在《日本的世界观》中,以三个人物凝练地串起日本两百年的变化。为此,我们采访了主要研究中日文化关系史、隋唐对外关系史的日本姬路独协大学人间社会学群教授石晓军,与他聊了聊日本的世界观的变迁。《日本的世界观》马里乌斯·詹森著,柳立言译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年2月版01“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是上千年中日交流融汇的结果新京报:在新冠肺炎疫情里,日本捐来的口罩感动了许多中国网友。其中,像“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等鼓励口号引起网友热议。这也体现出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你身在日本,据你的观察,普通日本人对于中国的疫情是什么样的态度?石晓军:在中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日本社会各界旋即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对中国的抗疫进行了积极的支持。您提到的支援物资包装箱上写的一些诸如引自《唐大和上东征传》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等各种来自于中日古典的诗句,更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此举使得这些本来是小众化,即只是少数专业研究者才比较熟悉的东西,普及到了一般民众中间,成为中日两国民众共有的精神财富。而且,这种现象也集中体现了中日两国对于汉字以及用汉字书写的古典诗文的共享、共鸣程度之深。有人惊诧,日本人何以对这些以中国古典形态撰写的诗文也很熟悉?其实,这一点刚好与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有关。正如俗话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言以蔽之,这种情况乃是长期以来中日交流的结晶之一,可以成为我们观察中日交流史以及日本人对外认识的一个窗口。除此之外,与年汶川大地震时同样,日本国内各地也出现了一些街头募捐等活动。即便在口罩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商店也并没有涨价,有些商店甚至反而降价出售口罩。而当面临口罩将要断货,不得已实行限购时,有的商店在日文告示上说一人限购一包,但在中文告示上注明一人可以购买两包。同时,媒体、学校等还以各种方式向民众以及未成年的小学生们强调,不能将病毒与特定的国家等挂钩,当出现感染者时,只说性别、年龄,不提及其姓名及国籍,尽力避免一切有可能使人感到有歧视感觉的现象。上述这些情况,都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日本民众的一些自发反应。其不仅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人文关怀,更是上千年中日文化交流融汇的结果。这些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耳闻目睹,的确令人非常感动。通过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自媒体的报道,上述情况也不同程度地为中国网友们所了解,并因此感动了不少中国人,引起了很多共鸣。随后,中国网友的反应也迅速反馈到了日本,两者共同促使中日民间舆论出现了一股暖流。尽管期间也出现了个别人大量囤积口罩并高价转卖,以至于出现了疫情扩大至日本时,日本民众反而买不上口罩的现象。但总的说来,这次围绕新冠肺炎疫情中日两国民间舆论的互动,乃是近年来鲜见的中日民众交流的一个突破,可以作为研究中日两国相互认识问题的一个范例,值得两国朝野以及相关研究者们重视。02日本在借鉴中国文化时更易挑选取舍新京报:能否简要地介绍一下《日本的世界观》这本书?在书里,詹森提到,虽然在历史上,日本受中国影响很深,但日本没有对中国的所有东西不加选择和修改地接受,日本本身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始终显著。为什么日本在接受中国文化的时候还能保证本身的文化价值呢?也因为如此,日本对中国通常抱有一种矛盾心理,这是中日关系最不寻常的地方。这种矛盾心理体现在哪里?是怎么形成的?石晓军:M.B.詹森这本书的原名叫JapanandItsWorld:TwoCenturiesofChange(日本及其世界:二百年的转变),该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年出版,到年日本的岩波书店就推出了日译本。由于我研究的领域之一是历史上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问题,所以很早就有该书的日译本,并通过日译本了解了全书的基本内容。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在拙著《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台湾商务印书馆,年)的执笔过程中,除了中日的先行研究之外,也注意到了一些欧美研究者的观察研究,詹森的这本书就是其中之一。詹森作为20世纪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日本史研究者之一,其重点研究领域是江户时代及其以后的日本。他这本书并非一部研究专著,而是三次讲演的记录,篇幅不大,可读性很强。在这本书中,他分别选取了18世纪七十年代翻译西方医学书籍的杉田玄白(-)、19世纪七十年代执笔起草岩仓使团历访欧美诸国报告书的久米邦武(-)、以及活跃于20世纪中后期传媒界的松本重治(-)为叙述的主线。全书通过这三个人物,观察了18世纪中期以后二百年间日本人对外认识即世界观的变化轨迹。换言之,这本书中译本的书名虽然叫做《日本的世界观》,但全书并非从古至今全面讨论历史上日本的世界观问题,所述只是两百年来的情况。年的日译本以及年香港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初版的书名,都保留原书的副标题“二百年的转变”,或许更能凸显这本书的重点。马里乌斯·詹森尽管如此,但要谈及18世纪以后日本对外认识的转变,则势必要涉及之前的情况,否则将无法说明其转变。所以,在詹森这本书里,也用不少篇幅谈到了近代之前日本与中国的交往大势以及对华认识问题。而这一方面,也正是我
转载请注明:http://www.soyingyong.net/fyzqzz/115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