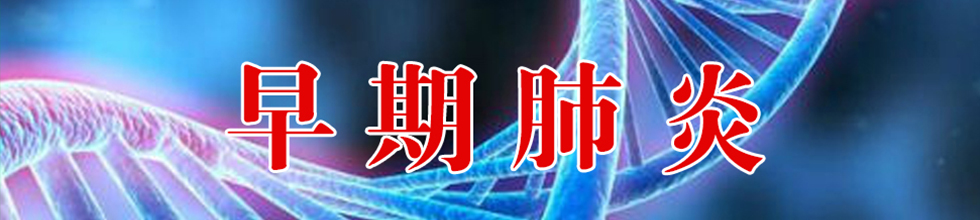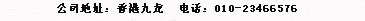在武汉ICU里,护士们所见的悲喜与无常
来源:早期肺炎 时间:2024/3/7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程靖截至年2月26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已感染全球人。在病毒最为肆虐的湖北武汉,新冠病毒累计造成人感染,死亡人,治愈人。在这场疫情中,成千上万名医务工作者用他们的勇气与专业,共同组成了抵御疾病的“长城”。东方网·纵相新闻采访了5位这1个多月来战斗在一线的护士。她们有的是武汉“土著”,有的是外地驰援而来;她们用悉心的照料,帮助着所有症状初现,或是生命垂危的患者;她们在雾水模糊的护目镜后面,目睹了疾病带来的恐慌、悲痛和斗志;她们中有人与恐惧的心魔不断斗争,有人重新定义了“岁月静好”,有人认为他人眼中的“逆行”只是职责所在。过去的1个多月,她们经历了什么,又有过什么样的心绪?(图说:医院的护士们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忙不赢的第一道防线和记者通话时,医院发热门诊的护士长王洁正在给护士们排班。王洁刚刚得空休息了两天,护士们也将轮流休息一下。王洁说,大约两三周前,来发热门诊就诊的病人渐渐少了起来。医院一个个投入使用,从2月10日左右开始,一天接诊的发热病人从~人,下降到最低60~70人,目前基本在人以内。医院接收新冠肺炎病人的“第一道防线”。她向记者回忆,最高峰时,医院发热门诊一天能接诊多个发热病人。1月23日,武汉封城起,大医院的发热门诊。医院都是一床难求,医院等不到床位,大量发热病人又医院寻求医治。王洁说,恐慌情绪让不少患者宁可坐一张板凳、一张躺椅也要等在发热门诊里。“那时的发热门诊就像一个特别繁忙的菜市场,乌压压的都是人,每个人都很焦虑,可能同时有10个人跟一个护士说话,护士也不知道她该怎么办、先应谁。每一个人都焦虑,医务人员焦虑,病人也焦虑。”“那时候很无助,想帮他们(患者),但没有床位,也真不知道怎么安置他们;护士工作的压力也很大,一个班7小时,一分钟一秒钟都停不下来,手不停脚也不停。实在是忙不赢啊!”在发热门诊,护士们除了要接诊、分诊,接待安置患者,协助挂号、拿检验报告,给患者注射、输液,给病情不好但没有床位的留观患者监测生命体征,还要抢救临时送来的急诊病人。“从早上8点开诊,一直到凌晨1点,人都是一波又一波。1点过后会稍微少一点。”王洁说,一些病人体谅护士忙不过来,对她们表示理解,说声“辛苦了”,护士们都很感动,但她也理解一些患者情绪不好,“等着看病等了那么久,你想他们情绪会好吗?”最近,来就诊的病人情绪好了很多——王洁特意着重了“很多”。不过,短暂的休息不代表战役结束——随着病房压力增加,王洁所在的部门已有一部分护士抽调去了病房,护理那些不断转院而来的重症患者。重症监护室里的气喘很揪心病房里远离喧嚣,却是和病毒与死神不间断的战斗。重症监护室里(ICU)里常常上演这样的生死时速:患者病情突然恶化,胸闷、呼吸困难、生命体征减弱——护士们匆匆赶来,开始心脏按压、面罩给氧、气管插管、上呼吸机,分秒必争,然后监控仪表盘上的曲线逐渐恢复正常——病人抢救回来了。(图说:上海护士滕医院重症监护室支援工作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随上海医疗队支援武汉医院东院护士滕彦娟,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上班。滕彦娟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ICU接纳的病人主要是指脉氧水平低、肺功能较差,或是伴有其他基础疾病、其他脏器功能损伤的病人。这些病人病情较重,“连喝口水,都会大口大口地喘气,像高原反应一样,听得很揪心。”滕彦娟说,“有的病人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所以我们就跟病人讲,有什么需求你就敲一敲,或者我们来猜一猜,你是不是要喝水,是不是要小便?哪里不舒服,我们给你喊医生?我们尽量让病人少说少做,减少他的耗氧量。”滕彦娟所在的重症监护室核定有20张床位,但重症病人多了,有时要加床。她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一名护士会负责5~7人。“我们基本没有看到过有空床位的现象,经常是在不停地加床。”但滕彦娟也表示,他们不怕加床,“我们来武汉之前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只要身体吃得消,累一点也没事。我们也希望多收一点病人。通过正规的治疗,能够治愈出院的病人也多一点。”在隔离病房,没有护工,也没有家属陪同,护士要负责病患所有的生活护理,包括吃饭、喝水、排便、清洁,甚至打扫卫生、搬运氧气,对医护们的体力都是极大考验。病毒的威胁无处不在,护士们每天处理病人的体液,排泄物、痰,都会接触到大量的病毒。尽管,医护人员都做了最高等级的防护,但来医院东院、医院支援的护士文佳也告诉记者:“我们给一些打了无创呼吸机的病人喂饭,把他们的面罩拿下来后,他们不停地喘气,这还是有一定风险的。”病毒是一个危险因素,除此之外,对于她这样长期在ICU工作的护士来讲,“困难也还好。”(图说: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护士在护理病人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钟小锋是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护士长。她告诉记者,医院ICU的护士原本每个班工作8小时,疫情开始后,护士们穿着防护服工作对身体消耗太大,就改成了6小时,“4小时一班是最合理的,但现在物资还比较紧张,只上4小时不太现实。”钟小锋说,过年期间是最忙最累的,小年夜那天甚至到凌晨三点半还结束不了工作。后来,浙江、内蒙古支援的医疗队陆续赶到,人手紧张的状况有所缓解,“现在护士们连上4天班能休息两天,可幸福了!”“我担心病人的结局,和我的结局”“出发的时候心情是有不舍的,也有担心。”滕彦娟去年刚刚当上二宝妈妈,离开家时,小宝才不到10个月。报名支援武汉后,滕彦娟被安排到了第二批,1月28日飞抵武汉。(图说:滕彦娟和医院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回想起当时心情,滕彦娟说:“只知道我是来支援的,但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一直在说’注意防护’,但还没体会到要怎么做。”1月31日,滕彦娟和同事医院重症监护室接班,很快就领会了新冠病毒的“无情”:“那天,我们当班的4小时里就抢救了3个病人。下班的时候,看到病人的家属在楼梯边上号啕大哭,哭得我们组的队员都心酸得不得了。”滕彦娟说,即使现在想到当时患者家属的哭声,她都会流下眼泪。ICU里和死神争分夺秒的交锋,让滕彦娟感到了紧张,“真的第一次看到连喝一口水都喘得脸憋的通红的病人……加上网上看到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报道,心理压力确实很大。”滕彦娟说,那几天都睡不着,“一是担心会不会被传染,二是担心这么多重病患者,我们怎么做?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样?我的结局又是什么样?”同为上海医疗队员,来医院东院的护士医院时,也遭遇了这样的心理冲击。“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很多岁数大的,都有些合并的疾病,身体机能比较差。来了之后,看到有病人病情恶化,然后离开了人世,对我们来说创伤挺大的。”钱晓说,医院工作,但平时没有目睹那么频繁的死亡,“现在感觉死亡就在你身边,而且来得很快。”滕彦娟说,到武汉的第一周,她有些焦虑、悲观,一直失眠。没有休息好,她觉得体力一下子跟不上了,好在队友是参加过年抗击“非典”的资深护士,在自身防护上一点一点地带教,“她和我说,’你一定要心宽,这种病毒没有多可怕,我们只要做好防护,不会被感染的。’”随队心理医生告诉滕彦娟,队中有类似状态的同事不在少数。滕彦娟告诉记者,在有着防治传染病丰富经验的同事的帮助下,加上心理医生的疏导,差不多经历了一周多的时间,心理负担慢慢地放下了。滕彦娟告诉记者,她护理的病人中有一位年长的乐器修理师,人很乐观开朗,总是对她说:“你们上海医疗队太不容易了。等我好了,一定给你们唱武汉最有名的《武汉大鼓》!”滕彦娟说,虽然来时身体各项指标比较差,但老先生的病情也在逐步稳定,“我们天天都去给他加油,我说您一定记住,我一定要听您的《武汉大鼓》!”(图说:医院重症监护室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相比逐渐适应的上海医疗队员,对于从疫情初始就已打着十二万分精神的钟小锋来说,病房里的阴云始终没有散去。钟小锋告诉记者,早期第一波的病人都顺利出院了,但后来随着病人的分流,被送来的病人几乎都是危重症。“我们最高峰的时候,ICU收满10个病人,9台做血液透析的,6台上了ECMO(人工膜肺)。我们这里的病人都做了气管插管,和医护没有办法交流。加上不断地有被感染的医护人员被送来,这段时间上班上得比较压抑。”钟小锋说,每当有病人不幸离世,大家心情都不好受,北京来支援的一位教授便会在
上一篇文章: 基因指纹破案美国这场会议最终导致245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转载请注明:http://www.soyingyong.net/fyzqzz/10589.html
最新文章